我是一九三八年元月调青训班工作的。我原来在红军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当过一段时间共青团团委委员和团委书记。红军改为八路军时我就到了延安,入抗大第一期一大队学习了三个多月。当时冯文彬同志到抗大要干部,要做过青年工作的。我年龄二十二岁,过去又当过团委书记,就被选中了。
到了安吴堡,我可就成了有名的“土包子”了,是文彬同志开玩笑叫出名的。我没有上过多少学,年纪很小就参加了红军,一下子让我到青训班做学生工作,简直不知道如何做法。自己社会知识浅薄,文化水平低,总感到和“洋包子”们在一起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每期学生毕业临走时,要求给他们题字,我能写几个大字呀?我很为难,就去找冯文彬同志,要求干脆让我回延安,去前方打鬼子,干这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我不行。“要回延安不行。干不了先慢慢试一试。”文彬同志没有答应我。我只好服从组织。这样,我就从一九三八年元月底一直干到一九四○年青训班奉命全部撤退。
青训班确实是锻炼培养人材的一所青年学校,我们这些文化不高的工作人员,也在实践过程中强迫自己努力自学,掌握适应教育工作需要的新本领。我开始在教务处军事科当教员,到第五期时兼任学生第五队队长,一九三九年的七、八月份又担任了生活指导处处长,九、十月份刘瑞龙同志调走后,我担任了代班主任,和张午同志一起负责青训班的全部工作。
在青训班工作的两年多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广大青学生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师生之间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是永远值得记忆的。
青训班的组织机构也是随着青训班本身的发展需要而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班部。班部由正、副主任及教务、生活指导、总务处组成。处以下设有科,教务处设有教育科、军事教育科;生活指导处设组织科、宣传科、党总支部、地方工作科及学生总会;总务处设会计科、总务科、卫生科等。我到青训班时已是第四期了,校址已从云阳镇迁到安吴堡。这个时期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教务处处长刘瑞龙、副处长郭思光,生活指导处处长张琴秋、副处长史洛文,总务处处长石济时等。
青训班的干部(包括教员和各科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来自延安中央党校、抗大、陕公,但大批的是从学生中培养选拔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干部总数达到250—300人。从五月到年底一段时间,大批学生奔向西安要去延安寻找救国之路。因此,每天来安吴的青年源源不断,一个月少则六、七百人,最高达千人以上。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留学生和华侨爱国青年。为什么呢?一是抗战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亲眼看到蒋介石玩弄卖国投降的阴谋,人们爱国没有言论自由,救国得不到人身安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祖国大片河山奉送给日寇。因此,绝大多数热血青年抱着救亡图存的愿望来到西安,去延安找出路,二是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到延安,我们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在全国人民中影响很大,深得人心,要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三是地方党组织长期在青年中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白区青年工作有基础的河南、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地下党动员了很多青年及学生来安吴堡,有的还是党员;四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西北学生中影响特别大,学生心向共产党,向往陕北。当时的安吴青训班实际上起了向延安输送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转运站”的作用。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六月,西安地下党送的学生最多,有二中、西师、西高、女师、西北临大等。海外华侨也很多,都是经过华侨团体介绍来的。除学生之外,还有青年工人和职员、军人。
青训班的教育内容大致分四个方面:(1)社会科学常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2)中国革命运动史,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简要兵器常识及军事常识;(4)简明哲学原理。每期时间是一个月,因为时间一长就没地方容纳了。后来期数互相交叉,流水毕业。到一九三八年三季度后,有一些队延长到两个月。专业队,如文艺队、军事队、速记班等就不受时间限制了。
我们青训班的基本方针是向一切爱国的青年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具体实施中贯彻实行统一战线,使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得以具体体现。以上四方面课程,最基本的课程还是统一战线。但是,讲统一战线不是没有斗争的。泾阳县的安吴堡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假合作真反共的两面派伎俩,随着他在华北等战场上的失败愈演愈烈。一九三八年后期,泾阳地方反动势力不断向安吴堡进行侦察和捣乱,还在附近的云阳镇、鲁桥镇、三原县城和泾阳县城设立秘密督视据点。在青训班附近新办了一些国民小学,派来了经过国民党训练过的一批教员,虽然不全是特务,但很多是接受了任务来向我们作斗争的。他们在当地农村青年中进行所谓“三民主义”宣传教育,挑拨青年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们的学生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怀表、手表的人不少,他们就派特务打进安吴堡,装扮成修表的手艺人,明目张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学生到卖小吃棚子里吃点东西时,他就鬼鬼祟祟地探听消息。后来,大家都认出他们有的是危险人物,就想出很多办法挤他。例如青训班部办了简陋的青年食堂,供学生买小吃等方法。他们觉得实在呆不住了,只得搬出安吴堡,到鲁桥镇等地去了。还有些特务,化装成小商小贩,卖糟的,在安吴堡村里和附近农村中发展特务,在群众中制造谣言,乘机接近我们的学生。有时他们也借用“参观”的名义,组织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受骗的青年学生和特务到青训班来“参观”,实际是搞实地侦察,索取情报。当时西安有两个大叛徒——叶青和柳林,办了个《抗战与文化》刊物,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一本一本地免费向我们青训班送,没有人理睬,把它压起来,只是在国民党派人来视察时才摆出来,走走形式就了事。
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延安实行封锁,掀起了反共高潮,情况日渐恶化。国民党反动势力加剧了对安吴青训班的封锁,通往安吴堡的各个要道——咸阳大桥、草滩渡口、三原城鲁桥镇、泾阳城及泾渭河畔各渡口点,到处都设立了卡子、哨所检查站,拦截到青训班学习的各界青年和学生。同时还在安吴堡通往延安和陕北的道路上扎下卡子和驻上军队及稽查人员,完全断绝了安吴青训班与延安的通道。国民党特务采取欺骗手段,向不明真相的学生散发他们的所谓招生简章,说他们也在三原、咸阳、西安办有青训班。实际是集中营。有一些学生因此上当受骗,陷入虎穴;一些来安吴青训班的学生在途中被绑架,进了青年劳动营。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生来源大大减少了,周围形势日趋紧张起来。但不管国民党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怎样封锁我们,我们青训班依然坚决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去延安的道路堵死了,我们就从关中边区绕山道去延安。一方面,我们从政治上大力宣传统一战线的各方面的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事例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和群众,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夏,国民党泾阳县县长王某来青训班要给学生讲话,我们出于统一战线的关系,不好拒绝。他没讲几句就胡说八道起来,什么“你们这些青年学生要找前途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十足的找错了。你们应该跟蒋委员长走,到那里才有光明前途……”还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学生们象是看小丑表演似的,阵阵发笑。他讲话后,乔木同志走上去,针锋相对地而且十分策略地据理讲了青年的前途,讲了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绩……,学生们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心里的爱憎,气得那位县长灰溜溜地离开安吴堡。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防范,把学生组织起来,生活行动都军事化,又成立了一个军事队,进行军事训练,每晚站岗放哨,安全巡逻。中共陕西省委给了我们二、三十支步枪,一挺机枪,一些手榴弹。这样我们的教学依然按照《大纲》实施,学生们的情绪不仅没有因环境恶劣而受到影响,相反,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无论是白天站岗,还是夜间巡逻,一个个精神抖擞,用临战的姿态,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我们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有利条件是:1.有地方党的帮助;2.有安吴堡周围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3.有青训班学员坚强团结和抗日救国的决心,相信跟共产党走就有光明前途;4.有党中央及陕西省委的领导,能够及时得到中央及省委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春,从豫西、晋南和陕西各地来了一批农民青年,一百二十人左右,我们编了三个队,总的叫军事队。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随时做好了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一九四○年四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来电报要我们撤退,陕西省委向我们传达之后,我和张午、刘昆等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和上级要求做好学生的思想动员,做好地方群众工作以及撤退的一切善后处理,抄小路安全地把学生送到了延安。
安吴青训班,在我们党为了夺取抗战胜利需要人才的时候,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用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爱国抗日”“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把成千上百的青年——各族各界的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加以短期的训练,使之受到马列主义科学的启蒙教育,树立起为人民、为祖国而献身的革命人生观,为中国革命队伍输送了一万二、三千名有理想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而这些人中,很多后来都成为党的高中级领导骨干。这在青运史上是空前的、了不起的成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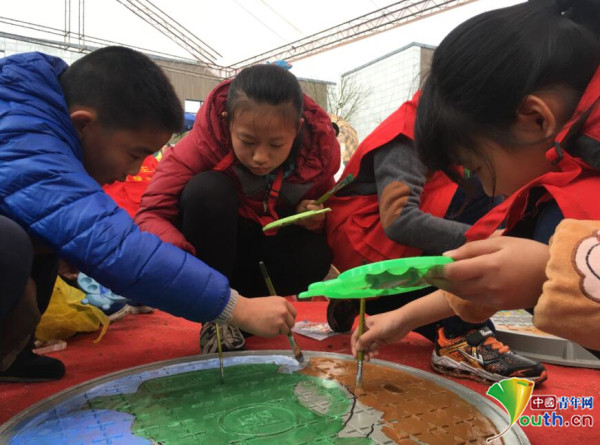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