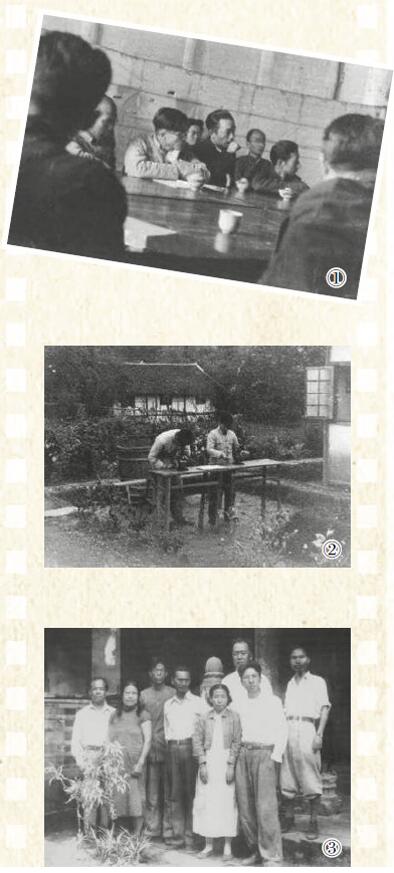
一天会比一天美好
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16岁。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一年级,暑假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那时懂点事,但不成熟,读报中看到宋哲元每次谈话都是“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和平和平,和就是要平,平就是要和”。但日本人一动手,中国人想和平也和不了。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在当时也是一座大城市,居然没多少日子就被日本人占领。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们也只好迁回湖南老家。
以往回湖南很容易,坐火车从北京到汉口只需几天。我们那次一走啊,就是40天。北方打仗,铁路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去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离开北京那一天,天气很凉,火车站里人很多,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四处弥漫着亡国的死寂。一个多月后回到老家,一个姑妈见到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的脸原来很圆,一路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
到了长沙还要继续读书,因为我从北京去的,很不适应。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在北京读书接触白话文比较多,湖南的中学生古文功底好。考大学时,我的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能考入西南联大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我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在西南联大,我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去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朱自清先生的课,钱锺书先生的课……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他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联大的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气氛。
回想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是不等于钱多,那么,美好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艰苦,可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也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的所在。
(任姗姗、何桂锦采访整理,部分内容摘自《上学记》,速写罗雪村)
李约瑟相机里的西迁浙大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这也被后人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这次西迁途经赣、湘、粤、桂4个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学院的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等。据说,在70年前,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时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54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出版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序言中他告诉读者,他1944年考察疏散到湄潭的浙江大学,结识了校长竺可桢和王琎、钱宝琮等学者。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宣读了李约瑟的贺词,特别提到三位已故学者竺可桢、王琎和钱宝琮,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他们的启发。十多年前,我已搜集到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走访湄潭浙大的不少文献资料,唯独没有发现那次访问的历史照片,颇为遗憾。
2008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捷克籍在读博士胡吉瑞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祖父钱宝琮与吴文俊在数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我立刻回信,并顺便请他在研究所查阅是否存有李约瑟湄潭考察时的历史照片。胡吉瑞复信曰:“李约瑟在湄潭拍了一些照片,其中两张可能有您的祖父,但是我们都不敢确定。”他还从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找出了李约瑟自制的“钱宝琮卡片”,卡片将钱宝琮称之为“中国数学史杰出权威”。第二天,胡吉瑞又来信说:“李约瑟在湄潭文庙拍的照片都不太清晰,有的还有双重曝光。”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喜不自胜,立刻回信:“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一手资料,因为它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你提供的照片来看,我已认出了王琎(戴眼镜,有点谢顶的老者),他右旁边很可能是祖父,由于是背面,而且不清楚,还需要再看”。时隔不久,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莫弗特专门来信,请我进入其馆藏网页,要我辨认李约瑟湄潭照片中的浙大教授,还允许我下载并公开使用加有其网页标签的老照片。
如此珍贵的浙大照片岂能一人独享!2009年1月,我带上照片去拜见106岁高龄的贝时璋先生。老人家手拿放大镜仔细地查看照片,兴奋地喊出王淦昌、王葆仁、王琎、丁绪宝等教授的名字。我又将照片分送给诸位教授的后代,也捐赠给了浙大档案馆、湄潭的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
李约瑟与浙江大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原计划在浙大逗留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的东西太多,对浙大的学术成就非常惊讶,因而留了整整八天,称“浙江大学是与在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可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他为英国《自然》杂志撰写了亲临浙大的所见所闻,并将自己拍摄的几张浙大照片刊登在他与夫人合编的《科学前哨》(文献)和《中国科学》(摄影集)上。
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包括校长竺可桢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学术会议(图①)、研究人员在试验田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图②)以及营养学家罗登义、生物学家谈家祯等做实验的照片。
70多年以前的照片已不够清晰,并且还有重叠现象,说明李约瑟当时操作相机的水平并不高明。然而,作为当时的科学史家,他适时捕捉信息,及时按下快门,定格历史瞬间,已是相当可贵。
李约瑟拍摄的浙大照片不仅见证了学校西迁办学的艰辛,记录了浙大人可贵的求是精神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而且填补了西迁浙大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资料影像的空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浙大西迁史乃至中外科学史最为珍贵的史料。
烽火中的西南古迹考察
杨雪梅
今年上半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受到各方的关注。目前,出水文物已超过万件,不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站就设在彭山县汉崖墓博物馆内,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考古人在抗战烽火中所进行的川康古迹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科学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和山东龙山的城子崖为代表。战争爆发后,两地的考古被迫进入到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然而,田野考古的炬火并未因之而熄灭,广阔的西南成为这一新兴学科勃兴的又一主场。
川康古迹考察由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馆前身)、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的人员联合组成。在李济的领导下,考察团从1941年5月正式开展古迹考察和文物发掘工作,以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永陵为代表,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吴金鼎、曾昭燏、夏鼐、高去寻、陈明达、王介忱、赵青芳……他们构成了考察团的基本力量,也成为今天的考古人经常回望、不断汲取力量的名字。
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1928年在山东城子崖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区别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193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主持了云南苍洱的考古发掘。他是此次川康古迹考察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夫人王介忱也是伦敦大学的考古学专业毕业,无偿地参与了他所主持的项目,使中国的考古发掘从此有了女性的身影。
曾昭燏,中国杰出的女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中央大学胡小石的得意弟子,1937年获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战争爆发后舍弃在英国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彭山崖墓发掘期间的后勤工作、后期整理、服饰研究等繁重工作均由这位杰出的女性完成。
当然还有夏鼐,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1939年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返回了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这位领导和组织了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大学者,其考古生涯正是从川康古迹考察团开始的。他承担了六座崖墓的发掘工作,并留下了珍贵的发掘日记。
陈明达则是古建筑学家,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学习古代建筑,是刘敦桢的主要助手。抗战时期曾在西南35个县进行古建筑考察。为了加强考古中建筑学的研究,考察团特别邀请他来负责崖墓古建筑部分的测绘和摄影。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众成员在彭山县江口镇东南的寂照庵内的一张合影(图③)。寂照庵是他们当时可以找到的最好居所。
在半年多时间里,考察团先后探明崖墓共900余座,发掘了8处遗址、77座崖墓、2座砖室墓。1942年12月,严寒的冬天来临,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不得不停工撤退。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分装三条大船,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总计达22吨的文物,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成为目前南京博物院颇为重要的收藏。
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第一次证明了崖墓这种四川特有的墓葬形式为中国本土文化之产物,以实物形式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四川彭山地区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寨子山550号崖墓出土的秘戏石刻,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其最新开放的雕塑馆展出。
今天你去成都,永陵博物馆依然是不错的选择,琴台路也是当地人喜欢聚集的繁华之地。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是抗战时期中国考古人科学发掘的首个古代帝陵。永陵未发掘之前,陵墓高大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修建了现代的琴台建筑。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突然被一道砖墙所阻,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断定其为重要的古墓葬。1942年秋,冯汉骥等考古人员进行了第一期发掘。1943年早春,川康古迹考察团结束了在彭山的考古便前来支援。吴金鼎作为团长,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莫宗江、卢绳等也一同前往。由于科学发掘,中国这座唯一的建于地面之上的帝陵,出土了王建本人的石像雕刻、重要的玉册、玉大带以及雕刻有24乐伎的棺床……郭沫若曾说,若是在和平年代,这样的考古发现怕是要轰动世界……
李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从重庆坐船要走三天,没有基本的药物,甚至没有纸张可供书写,没有印刷设备来出版书籍,但有六年的时间,一大批文化机构栖息于此。这里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13万册中文图书、上万册的西文书籍和两万册中外杂志成为做研究的最好保障,大家把借书说成是“上山去取经”。这里的九宫十八庙、板栗坳、张家祠堂见证了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史语所的《六同别录》的完成……
西南地区的考古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水准,丰厚的收获也是抗战中的奇迹。而那些在李庄一面接受最为艰苦的乡村生活,一面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先生们,才是中国文化奇迹的重要创造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7月06日2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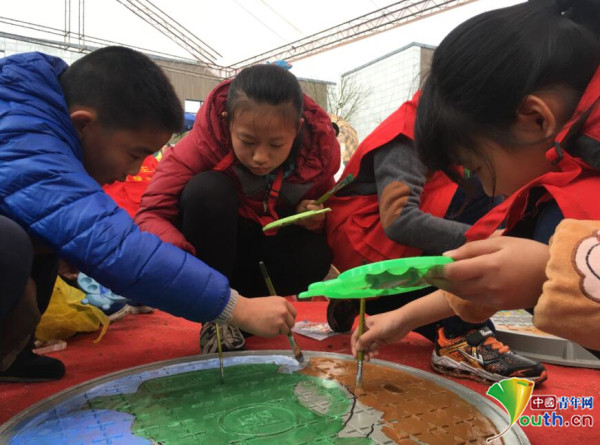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246